本文作者為廖翊如,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楊逵逝世三十五周年,令人感傷一個時代的結束,總是那麼的倉促,也令人不捨。時光一瞬,楊逵精神是那堅毅的孤狼形象,以及永不放棄的壓不扁的玫瑰,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台灣反殖民運動的歷史。雖說現下中學教育已收錄了楊逵的作品,但黨國體制遺緒的幽靈依然壟罩於教育體制,讓楊逵的身影依然在台灣社會缺席。而與他併肩面對強權壓迫的葉陶,更鮮為台人所認識。

楊逵的生命路徑與台中有深厚淵源,1935 年台灣文學創作的風華年代,楊逵的台中生命地圖,首站勢必以梅枝町的首陽農園為開端。這是標誌楊逵第一波文學創作顛峰的地點,也是楊逵與日本友人入田春彥警官的跨種族與身分階級象徵的地點。
關於楊逵的生平事蹟,孫女楊翠所撰寫之《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已經多有著墨,楊翠稱楊逵一生都是夢想家,都在發大夢與實踐這些夢想。
但大夢想家楊逵背後那條牽引著他,使他不致迷失方向,並能堅定向前的風箏線,線頭卻是牢牢攬在葉陶身上。
葉陶,「出生於一九O五年,高雄外海旗後町(今天的旗津)人,打狗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南女子公學校附設教員講習所,受訓八個月,結訓後,回到母校打狗公學校任教,其後轉調高雄第三公學校。」葉陶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日治時期,一般民眾對於女性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從事工作,拋頭露面是難以接受的現象,葉陶已經自力更生,稱呼她為新女性也未嘗不可。
女性獨立自主已經不常見了,何況是陽剛味十足、充滿動盪不安的社會參與?但這些似乎對葉陶來說,不過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因為受到第三公學校的同事簡吉的號召,葉陶對農民處境感同身受,因此跑在前線參與社會運動。楊逵正是在農民運動來到鳳山演講的場合遇到葉陶,兩人因為葉陶請楊逵在扇子上題字而結下姻緣。
根據楊逵口述的內容:「我們認識了。她要我在她的扇上題幾個字。當時日本人把我們的民族主義者叫做「土匪」⋯⋯我想起了這些,就在她扇上寫了「土匪婆」三個大字。因此她出名了,「土匪婆」成為她的別號。」葉陶因為受到簡吉的感召而參與社會運動,「土匪婆」仿佛是楊逵送給她的身分,葉陶或是受到革命情感的激情、或是對新身分的認同,她從此與楊逵結下不解之緣。
「土匪婆」葉陶與楊逵在一九二O年代的愛情,在當代的驚世程度著實令人捏了一把冷汗,兩人在尚未結婚時,就已經同居。「楊逵與葉陶在彰化組織讀書會時,租屋同居,賴和醫院,是他們的書房、聚會所、討論室,更是特約醫院。⋯⋯在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呼聲高漲的一九二O年代末期,未結婚而同居,在他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我們對制度和形式並不重視,人的結婚,最要緊就是雙方談話會投機,興趣相同,志同道合。這樣結婚儀式就不重要了。」
楊逵與葉陶的愛情故事,即便放到今天的台灣社會,恐怕還是難以見容於很多長輩;但是固執的楊逵、有海洋爽朗性格的葉陶,他們目光關注著更精神層次上的問題,因此俗世的傳聞、儀式、禮俗等,都無法以自身的重量在這兩位社運俠侶的身上套入繁複枷鎖。
令人不免好奇,楊逵一生都跟貧窮脫不了關係,甚至如影隨形般,手頭總是難以寬裕,甚至要到友人救濟的程度。那婚後的葉陶是怎麼看待這一切?楊逵的作夢性格,對葉陶的婚姻生活影響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在楊逵因「罪」入獄十二年間,葉陶又是如何苦撐一個家的?
實際上女性的樣貌在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而來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缺席的。
女性需要承擔的風險顯然相較於男性高,除了社會加諸其身的期待與性別刻板印象,例如認為女性就應該賢淑待在家中相夫教子,受到官方盯哨一定是因為品德、行為上不檢點等偏見;又或是孤家寡母的家庭,必然受到社會大眾的凌辱,女性參與社會運動要付出的成本顯然較男性高多了。

或許可以從友人之間的對話、青年學子與楊逵互動接觸時,描述的葉陶略知一二。楊逵的友人入田春彥警官在遺書上寫道:「葉陶女士:我認為最能夠俐落為我處理事情的人就是妳,因此我就不客氣地拜託妳了!」短短幾句話,道出葉陶做事的風格態度:沉穩、俐落、謹慎且令人放心。
又或是楊逵自己描述的:「我和葉陶時常為了金錢的用度起爭執。葉陶開朗樂觀,一心計畫生財之道;我是謹慎保守,只想簡約過日子。有回,我剛借來五十圓,葉陶瞞著我,拿錢借人想賺取利息⋯⋯」從這邊可以看出葉陶在婚姻關係中,相較起楊逵,對子女有更多的責任感。楊逵還在想著自己可以忍受貧窮飢餓的同時,他忘記自己與孩子們是不同的個體,他能熬過貧困,孩子們不一定能。
「這是葉陶當賣花婆的開始。她從前從事抗日運動,到處演講,認識的人不少,所以生意很好,意天可以有兩圓多的收入。當時只有三個孩子,開支簡單,勉強可以度日。」由此可知,比較社會普遍對丈夫/父親角色所抱持的期待,葉陶更像一個家庭的支柱,總為家人打算;甚至在楊逵因為白色恐怖入獄服刑時,葉陶搬到淡溝里(今國立科學博物館附近)購地,經營花園經營得有聲有色。
然而,當時的社會氣氛對待政治犯的家屬充滿歧視與偏見,暴力相待的情形普遍常見。
楊逵入獄十二年,子女為了謀生,四散各地⋯⋯十二年間,孩子們接續進入青春期,面臨生命困局;然而,楊逵也許無法真切理解,剝奪他們喜樂的元兇,不只是青春期,而是貧窮,以及國家暴力所營造的恐懼,還有它的衍生物。
楊逵不能想像,獄外的台灣,竟比獄中還詭譎。社會的冷漠,平庸者的邪惡,對受難者家屬而言,是一副終生都無法解下的腳鐐手銬。
次子楊建回憶,父親被捕後,軍警不斷到家中搜查⋯⋯
這段敘述可以看出,身為政治受難者當事人,無法想像在外頭的家人竟受到如此不堪的對待,尤其是家中失去男主人之後,軍警的肆無忌憚,以調查之名行勒索、竊盜之實,讓葉陶與孩子們身心俱疲;尤其是楊逵去信要求家人寄藥錢時,一家人生活被剝奪、剝削的無力感以及心理負擔,只會更加沉重並造成彼此之間的裂痕而已。
楊逵的理想與性格固然使人敬佩,然而,葉陶的支持與無悔的付出才更叫人驚覺,當我們將目光放在楊逵身上時,殊不知背後那個曾經在農民運動場合意氣風發、爽朗而充滿鬥志的葉陶,居然甘願俯首為幼子、為丈夫忍辱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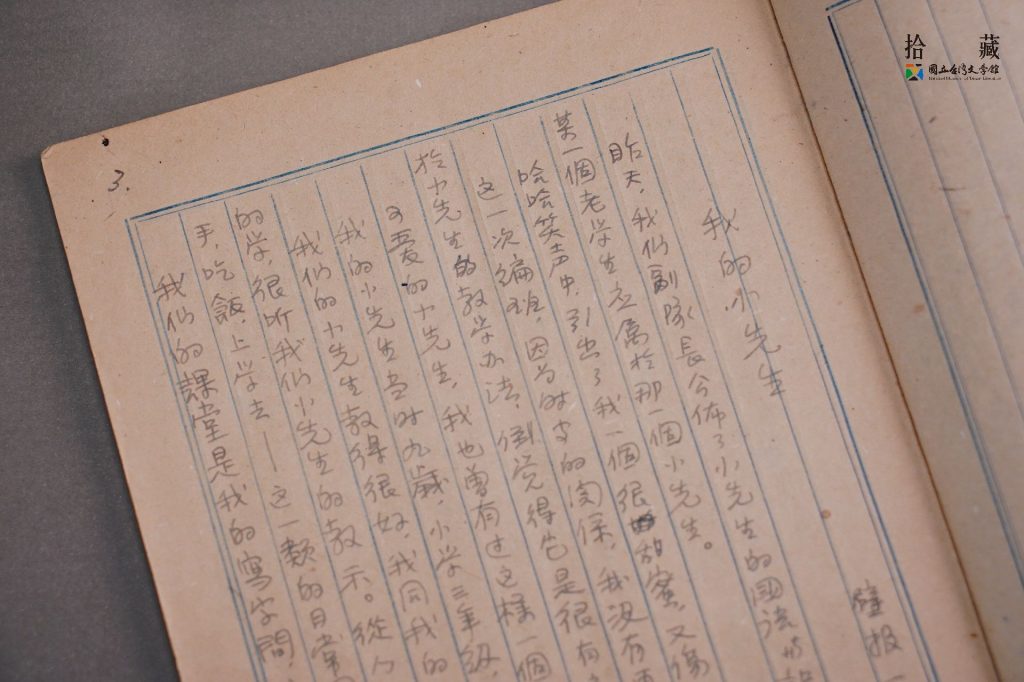
次女素絹曾寫下她們到東海大學老師宿舍賣花時,母親被講師妻子羞辱的情景:
那個女人立刻氣忿忿地把花一摔,說:「你這賣花婆,賣花太貴,太愛錢了。」⋯⋯想當年,媽在大街小巷演講,抵抗日本軍閥,妳還沒出生哪!甚麼講師助教的太太,就這樣神氣。我不滿意的心,表現在臉上。媽看出我的心事,淡淡地說:「我四十歲賣花,人家喊我阿婆,現在六十多了,還不真是個賣花婆。」
「土匪婆」葉陶與楊逵併肩面對強權壓迫,她的生平經歷值得後人大書特書,期待透過以女性為主角的書寫方式,讓受難者以及家屬的面貌更完整,呈現給更多台灣人知道,在過去高壓專制的統治下,台灣女性承受來自外部如軍警、鄰里的壓迫而淬煉出的堅毅性格,以及對家庭孺子的溫柔之情,是怎樣成就了革命男性的風光,將台灣帶向民主自由的方向,這些女性功不可沒。

評論被關閉。